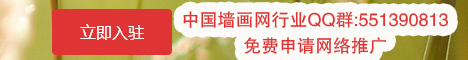在《美术同盟》论坛上见到王林的文章《 谁来批评许江》,王林此文,对众所赞褒的许江学术场氛提出质疑,并通过对许江《视觉那城》、《一米的守望》两本书的评论,引出了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一些深层问题。应该说王林的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感到王林用学术词藻和褒斥平衡把批评的核心问题、真实意义弄得模棱不清,尤其是爆炸架式的标题和文尾“仅以此文向许江学习,向许江请教” 的谦恭,形成一种暧昧的语境,呈显出投机性的反差。
以至吴鸿跟帖指出:“王林斯文除了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外,其‘捧’还是要多于‘批’,只不过比起那些不要脸的、直白的吹捧要高明一些。”
来看看王林话语形态的暖昧所在:
王林文章首先并列了《美术报》对许江的赞评,头衔与评论放在一起的众捧现象,和“好在许江与邹忌一样,头脑是清醒的,”并坚持人文学者立场的定性描述。接着展开对许江《视觉那城》的评述,认为“因其具体而深入,乃是艺术家写作中不可多得的文字…要说思想并非深刻,要说感受的确是细致入微。”。并引用长达三百字的许江散文字句为佐。在说尽溢美之辞后,才进入到“历史和权力的追向”,说到“许江以国家为本对城市的解读之不能使人信服”的原因。但王林对其原因的“追问”,也止于某种西方知识系统如列斐伏尔“第三空间”说的原则界定,并末针对许江的话语发生而进行深入的分析批评。
接着,王林在称赞许江“写得精辟”的一段话“但在北京带着一种近官的痞味,在上海则带上一份近商的‘娇’气”之后,又才指出“但囿于国家意识形态,许江不可能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的‘第三空间’”,这话明显是指许江的体制身份和意识定向。
在《视觉那城》中,许江对北京法国文化年晚会时某老外骑摩托车穿过天安门的行为发出民族主义的义愤,认为剌痛了“生命中的某种神性”。王林为了“以免陷入爱国与否的纠葛”,以《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成人化儿歌和宋冬《哈冰》来比较,倒底是为神性而感动还是为反神性而感动。王林文章的批评所指,此时才转弯抹角地、半遮面地表达出来。这种欲言又止,临渊却步的话语方式与耸人听闻的标题实在有悖。
细究王林文章标题,除了耸人听闻的发效目的外,还有模糊批评者身份,虚化文责主体的潜动机。由兹使我不得不透过王林式批评话语,来说说当下美术批评界的立场缺位、话语暧昧和心理投机。
什么是“批判”、什么是“批评”
这个问题之所老生常谈,实在因为美术界随时淡忘常识。如果不作界定提示,则随时可被搅和进恩怨是非。对于合格的批评家、理论家而言,“批判”是对精神现象的清理、对艺术问题的疏导、对人生关联的解读、对语言糸统的分析。这种批判是康德式的批判,而非“文革”式的批判。“文革”式批判出于政治目的、斗争哲学的口诛笔伐,是要把人整倒,把事情拿翻的话语武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文革”式批判至今潜移默他,遗传于中国文化人之中,以及受众的通常理解之中。自然也遗传于美术批评界。成为美术江湖的明枪暗剑。造成受众对美术批评的误读。
康德式批判,其批判对象只是精神清理、人文解读的载体,往往超越批评对象的个体性而上升到事物的普遍性。并无褒贬好误的现实指谓。
“批评”的概念,则是在康德式批判即精神观照前提下,针对具体作品作者,进行其思想轨迹、形式话语的解读。严肃的美术批评依据精神观照和理性导引。这种批评对于作品是镜鉴,对于作者是醒药。世俗的批评概念则是对过失的责问、对异已的清算。行政式的批评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含义,尤其是经过文革,“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是政治运动的代名词。令国人心有余悸,普遍持有对“批评”一词的敏感和忌讳。由兹,王林此文的标题之所“耸人听闻”,也在于巧借了受众对批评的普遍文革式理解,对行政式批评的敏感忌讳,尤其是针对许江这一关涉体制权力象征性的批评对象。
体制文化与权力话语
王林此文并未从许江话语的发生学机制去深入探究其社会学、文化学意义,而止于抽象界说和比较提示。其实王林没说透的批评目标,是由许江“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混同”现象引出的相关潜话语。
在中国的文化场景中,由于体制惯性、社会通习,许江的身份规定性必然超越许江艺术本身而成为其艺术的潜话语和附加值。这未必是许江的本意。乃是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的规定。从某种角度说并不由许江负责。这种身份混同,是所有担任大学校长、行政领导的学术专家们的共同现实命运。在中国的现实中,要求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截然分开,几乎不是一个技术性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由之,在艺术社会学意义上,许江们的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的混同,乃成为某种特殊文化的表征,即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
在计划经济和一统社会,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仅仅关涉肉身制约和精神恐惧。而在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体制文化、权力话语则可转换为现实利益和话语权力。体制化与权力方式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下中国的症结性现实。也是艺术多元化的构成方面。在今日中国,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正在走向江湖化,体制内外的艺术势力正在握手言欢,利益交换,资源共享。
在中国文化迅猛的市场化现实中,体制文化、权力活语之能固若金汤、余威犹存。乃是因为整体社会意识、文化界、思想界没有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即通过思想启蒙、制度选择达到人的自由和社会契约间的相互保障。也使本属于个人的精神追寻、思想自由往往依附于共性体制和现实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思想界、文化人的深层悲剧所在。
体制文化、权力话语生存于政治文明推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延续几千年的官本位观念仍佐佑着中国的普遍事物和民众心理。中国的大学校长产生,跟官员制度一样,无一例外都非依据学术与冶校水平而经民主选举、公开招聘。乃由自政治选择与体制内调配而产生。因之在面对大学精神、思想自由、学术公器之时,则便缺乏基本的说服力与权威性。这也是中国大学陷入行政化弊端,而难以步入真正的科学民主管理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给一些担任大学行政领导的学术人材制造了双重身份的尴尬。
体制文化的话语方式和艺术形态
平心而论,许江以大学校长和艺术家双重身份,在国内同样身份者中,是相对有思想有作为者。一个人的思想轨迹、话语方式和艺术语言,必然决定于其生存环境和角色身份。从许江九十年代作品《世纪之弈》到现在的装置、水墨等,始终带着一种在解构的现实中重新寻求秩序的欲图,许江在德国对国际现代艺术的咨询,使他领悟到时代的视觉振撼和人类精神架构解体的现实,他画面的北京故都、码头、围城振荡飘摇,那凌空巡弋、神秘莫测、翻云覆雨的手、以及他几乎所有画面上表现出的曾经分崩离折、万劫千覆而终归聚合的视觉归纳,都显现了许江对事物世事解构后寻求秩序的内在欲求。或许,许江的个人风格与体制文化权力话语的美学选择有着天然的适合与默契。从对其发生学、现象学的判识中,可以洞见其深度心理和审美意识的社会学、文化学基底。
王林的文章并未从艺术学理去探究许江艺术的端倪。而是在权力话语和体制文化的现实壁垒前临渊却步,嗄然而止,灵活地转向“承担苦难”的抽象话题和对许江“批判精神”的赞褒。
体制文化的话语方式表现为两种特征,一是寻求秩序,保持维护尊严。再是标立学术纯粹性,推祟雅文化样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秩序与尊严,往往以国家、民族的名义、道德责任、宏大叙事的标准发布。标立学术纯粹性,则是将秩序之外的精神范畴转化为学术标件化和技术性规范。推祟雅文化样式,是淡化消解精神指向,把心性境界全部纳入审美养颐、情趣修练的伪品位标淮。赵佶的院体绘画、瘦金体书法、四王的精典程式就是秩序、尊严和雅文化样式的产物。经孔子删的诗经、李龟年收罗的乐府,也不外这种规定。洞察体制文化的内在核质,就不难理解极富反叛的前卫艺术也可摇身转变为学院面孔的经典样式,原本来自民间底层苦难的忧患文本,也会逐渐变得错彩镂金、时尚光鲜。
他者形象的深处
在王林文章的第二部分,关于《一米的守望》中,王林注意到许江的见解“在全球概念与多元的旗帜下,不加批判地宏扬差异,并由此建构一个片面的他者形象以充实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想像…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实难区分于文化分离主义,而事实上,这种分离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王林认为许江对现代艺术自我颠覆和差异原教旨主义的讨论富有启发,但嗄然而止,尚未深入。
在中国,所谓“现代艺术的自我颠覆”乃是艺术的个人价值、自由运动在社会共性、体制条件下的对抗方式和消积解构。现代艺术自我颠覆方面和体制文化权力话语方面,其实都在相对于国际社会建构着片面的他者形象,以充实其各自的全球化文化想像。尤其中国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往往通过自虐的手段装扮成被虐的姿态,将苦难兑换成利益资源,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选择。而在体制文化权力话语方面,则通过片面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实施新权威主义。以差异性旗号实施文化分离主义。前者是在建构边缘他者形象,而后者是在建构价值他者形象。这两种力量和趋向都远离理性批判而依据现实规定。
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的确有着非抽象的特色和现定,但若从历史主义、理性批判和精神观照,仍必须诉诸服从于摈弃落后、控制、非人性因素,而追求文明、自由、普遍人性的总体目标。只有将中国的问题纳入这个总体目标进行理性观照,方能洞悉各种文化权力和艺术话语的实质和潜因,才能把中国文化艺术导入健康的方向。
关于批评界的立场缺位、暧昧投机
出于对批评的不同理解,人们对批评家资质有不同的认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必要的资质,首先是立场,其次是理性、智慧和通感。立场是批评家立人立职之本。失去其它,只有立场,你都还是个批评家,失去立场,徒具其它,你就不能被称之为批评家。理性是你追求真理,提升学术的保障。智慧是使你别成为书呆子的本事。通感是你对艺术事物的整体统悟和灵觉。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做人要厚道,别用文革式、行政式批评替代精神解读式批评。
王林此文虽有失于暧昧与忌讳,但仍不失于立场。察见亦不乏深刻之处。只不过其立场被模糊园润淡化。随着美术界与时俱进的江湖化,批评界普遍存在立场缺位。二流的批评充斥着严密的学理与正确的判断。以及大量的知识辞条超市,用于配套组装,应付各种批评对象。这类批评企图以话语替代意义。千篇一律,应景附丽,作态作秀。连骂人的腔调都是一样的。绝少见到坚守立场,直击性灵,暴露问题的血肉批评。大量末流的批评则堕于有偿报道式的胡吹乱捧。批评的暧昧投机在于利益利害的顾忌。中国的批评机制决定了批评对体制文化话语权力的依附。批评的独立性谈何容易?面对体制文化权力话语,精神解读式批评一旦捅破薄纸,便会招惹是非,被体制权力的依附者、体制现实的受益者、维护者们指责为“疯子”、“狂徒”、“愤青”。而这些体制现实受益者,维护者都是当年勇伐社会不公,摈击体制弊端的战士。
鲁迅曾有喻例:一个小孩满月,人皆拥贺。众口一致皆说这孩子有福有帝王之像将来必定大发。然一人曰这小孩必会死,此人遂犯众怒。其实帝王福分皆虚枉,孩子必死千真万确。这其间有一个谁都没法反对的理由,那就是在体制与权力的现实中生存。
体制权力追求秩序,艺术家追求自由,思想者追求真理。三者各有所属,有时集于一身,便难免人格分离,灵肉矛盾。人生须臾,心斋无穷,各择所需,好自为之吧。
写成此篇的目的,乃是出于对思想自由、批评独立的守望。文章标题沿借了王林文章标题,也同样有投机之虞。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字问题,那就是《谁来批评王林》的“谁”是谁?我认为应该是批评界的自省和志诫。
仅以此文与王林和批评界同仁共勉。
牟群2006,3,30记于四川美术学院面壁堂